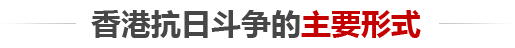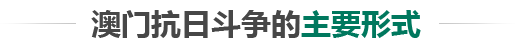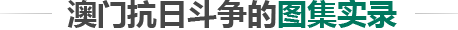抗战时期,澳门虽因葡萄牙当局所奉行的“中立政策”而未遭日本占领,然而,澳门的命运却始终与祖国休戚与共,澳门同胞也始终牵挂祖国的命运与伤痛。在14年艰苦抗战的历程中,澳门同胞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其中既有物质上的支持,也有精神上的共担与声援,甚至组织回国服务团投身于祖国抗战的洪流中。正如陈大白所言,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澳门爱国同胞的救国热潮空前高涨,出现了一股磅礴的气势,澳门爱国同胞特别是各界青年、工人、店员、各校师生等,采取多种途径冲破阻力,用各种方式展开爱国活动,这样一股爱国进步力量,乃是时势所趋,潮流所向,是难以阻挡和压制的。
第一,澳门民众从物质上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澳门当地所有报纸对事变的详细经过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报道,澳门当地各中小学也纷纷举行周会、时事会,向学生宣讲事变真相。中华总商会、同善堂、镜湖医院、中华教育会等四大社团发起成立“赈济兵灾委员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筹款活动,支援祖国抗战,澳门各界同胞纷纷响应,可谓开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之先声。而七七事变后,澳门同胞更是掀起了支援抗战的热潮,包括澳门四界救灾会、澳门各界救灾会等在内的各澳门同胞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并成为筹款义赈活动的主力。1937年7月,国民政府为募集军费发行5亿救国公债,澳门第一期便购买公债23万余元,第二期又购买1.4万元。 1938年9月,为声援祖国抗战澳门四界救灾会发起了全澳性的“义卖”活动,这一“义卖”活动除义卖商品外,还有酒店义捐房租、理发店义剪、茶楼义唱、舞场义舞、报贩义卖等多种形式的义赈活动,“既有店号个别义卖,又有整个行业举行集体义卖,有进行一天或多天,更有店号先后义卖多次的,全行业义卖不只情况热烈,更是高潮迭起。这次义卖运动,先后历时四十天”,共筹得义款10万余元,创下澳门四界救灾会的筹款记录,“这次义卖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泛,参加筹募工作人数之众多,是当年澳门筹募救亡活动中前所未见的”。 1939年“八•一三”两周年的澳门各界救灾会主办了大规模的“献金运动”,此次“献金运动”由于银行业、首饰行、洋货行等行业商人的参加和积极捐款,短短三天便筹款10万余元,成为澳门民众支援祖国抗战的又一次高潮,此次运动的范围“不仅遍及全澳门市区和离岛,更远至对海的中山县湾仔乡……无可否认,这次献金运动特别出色,异常成功,也体现出抗日救国洪流是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
第二,澳门民众救亡团体积极从事难民救助工作。抗战爆发后,葡萄牙当局为保护其在澳门的利益宣布澳门中立,从而使澳门成为战时民众避难所和中转站,大量难民涌入澳门。一时之间澳门人口从战前的15万人剧增至近40万。 为此,澳门各民众救亡团体积极从事难民救助工作,澳门四界救灾会、澳门各界救灾会、同善堂、镜湖医院等纷纷进行难民救济工作。同善堂便通过开办难民营、施粥等方式进行难民救助工作。镜湖医院也借出义庄作为施粥场所,仅据1941年农历七月初一的相关记录,领粥者便超过5000余人。应当说,这一时期澳门民众救亡团体的难民救助工作,卓有成效,使流亡难民生存得到了保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继而香港沦陷。澳门因虽未遭敌手,但周边地区已全被日军占领,澳门实际上成为了一座“孤岛”,澳门经济进入困顿期,各项传统产业都遭到巨大打击。不仅如此,大量难民继续涌入澳门,也给澳门社会、经济带来巨大负担,澳门由此进入“风潮”时期。与此同时,日本及澳门当局也对抗日救亡赈募活动大加限制,部分救亡团体也因活动艰难而选择解散。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团体从事小规模的秘密募捐,或将工作重心转向难民救济,其中澳门中华妇女会成为这一时期难民救助的主力。其通过设立平民粥场廉价售粥的方式对难民进行救助,截至1943年6月底,共计售出13267600份,并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各慈善机关及清贫学生,而其在望夏设立的粥场截至1945年9月共计售粥1332071份,极大地解决了难民的温饱问题。
而为解决难民的生存问题,澳门救亡团体和部分爱国人士还发起了“回乡运动”,为滞留澳门的难民提供旅费及援助,协助其回乡,从而有效解决了由于难民激增造成的传染病流行及难民大量死亡的问题,缓解了澳门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第三,澳门民众积极声援祖国抗战,使澳门成为中国南方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抗战时期,澳门民众不仅在物质上积极从事募捐赈济活动,支援祖国抗战,还积极声援祖国抗战。这一时期,澳门并未普及电台,新闻传播仍以报纸为主要形式,诸如《朝阳日报》、《大众报》、《新声日报》、《澳门时报》、《民生报》等中文报纸,承担起了抗日宣传的重任,成为澳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喉舌和阵地。《朝阳日报》、《新声日报》便通过每周出版一次《救灾特刊》的形式,大力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不仅如此,每逢重要抗战纪念日,各主要报刊便出版专刊或举行纪念会,以此宣传抗日形势,配合抗战宣传工作的进行,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决心。
澳门民众团体还以巡演的方式,以戏剧表演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如绿光剧社便在澳门和毗邻的中山县农村进行巡回戏剧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由廖锦涛、余美庆等人创办的前锋剧社也先后组织30多人,两次徒步到中山县东、西两线和各乡宣传,以歌咏、巡回演出抗战舞台剧和街头剧,召开演唱会等形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抗战宣传活动中,以澳门四界救灾会为代表的澳门民众救亡团体也成为声援祖国抗战的主力,积极组织各类宣传活动和宣传队进行抗战宣传,以激发民众的抗战救亡思想和爱国热情。1938年8月,为慰问武汉前线将士,澳门四界救灾会便发起了征集慰劳信运动,并组织工作队分头赴各学校、团体、单位进行征集。民众纷纷响应,有70多岁高龄的老人,也有刚满9岁的幼童。至月底,澳门四界救灾会共征集信件一千余封送至前线。1939年5月9日“国耻纪念日”,澳门四界救灾会便联合其他民众救亡团体,组织国民抗敌宣誓大会,到会人员举手宣誓“矢志为国,不做汉奸”,并合唱《保卫中华》,“场面庄严,气氛热烈。会毕还于当晚举行游艺晚会,当地上千民众到来观看,鼓舞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此外,流寓澳门的大批文化界人士也投身到抗日救亡宣传的工作中。高剑父为代表的“岭南画派”迁居澳门后,不仅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唤醒澳门民众的民族意识,还推动了澳门本地文化事业的发展。1940年1月,高剑父之高足关山月在澳门濠江中学举行个人画展,展出了其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从城市撤退》、《渔民之劫》等大批抗战画作,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深刻反映了抗战时期社会动荡给广大下层民众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一经展出便引起港澳地区的轰动,不仅吸引了广大澳门居民和各界人士前来,也吸引了香港人士专程到澳门观赏。流亡澳门的作家群体也创作了大量抗战文学作品,抒发爱国热情,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第四,澳门民众直接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早在1937年8月,廖锦涛等人倡议召开澳门救亡工作联席会议,成立“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赴中山县各村镇开展宣传工作。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华南局势空前危急,为保家卫国,澳门民众通过组织救护队、回国服务团等方式直接投身抗战。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便通过训练青年救护人员,组织救护队等方式,训练救护人员约80余人。澳门四界救灾会也积极组织回国服务团返回内地直接投身抗战,并于广州沦陷当日正式成立“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组织教师、学生、工人、职员、失业失学青年及流亡澳门的知识青年参加服务团。经过训练后,回国服务团团员主要从事宣传、战地救护、担任军队政治工作等任务。1939年在日军第一次侵犯粤北的战斗中,回国服务团第一、六、七队开赴前线,组织担架救护工作。
不仅如此,澳门回国服务团还直接参加战斗。1939年8月日军进攻深圳的战斗中,回国服务团第三队便组织和发动民众武装参加抗战和坚壁清野、支援游击队的工作,并领导200余名民众武装监视日军和掩护民众避难,并和游击队一同上火线作战,其中队员梁捷在战斗中不幸牺牲。1940年底,加入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独一中队的服务团成员侯取谦在番禺沙湾战斗中,为攻克日军炮楼英勇牺牲。 他们都是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杰出代表。
第五,国共两党以澳门为阵地,进行抗战救亡和宣传动员工作。抗战爆发后,澳门因葡萄牙当局推行“中立”政策,从而得以成为东亚唯一的“安全区”和对外联系的重要孔道。国共两党都已澳门为阵地,成立党部和党组织,进行抗战救亡和宣传动员工作。国民党便以澳门党部为中心,通过推动其文教工作的发展,宣传其抗战建国主张,开展打击日本和汉奸组织、鼓励华侨参加抗战阵营、协助侨胞回国等工作。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凭借澳门“孤岛”的特殊地位,在澳设立电台,积极开展情报工作,收集日本及汉奸的活动情形。
共产党也积极在澳门成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6月,中共广州市委派杜晓霞、廖锦涛赴澳门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1月,中共澳门支部正式成立,成立时有党员4人,到12月增加到6人。1938年1月,澳门支部改为中共澳门特支。中共澳门支部成立后,十分重视在澳门各社团及学校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并秘密举办党员培训班,给学员上抗战形势教育课。不仅如此,中共澳门支部还十分重视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并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投身抗日前线。
总之,抗战时期,虽然葡萄牙当局奉行所谓“中立”政策,但澳门民众却通过各种方式投身支援祖国抗战的洪流中,无论是进行筹款赈济,还是成立救亡团体,或是直接投身抗战前线,无论是物质支援还是文化抗争,无不体现了澳门民众与祖国人民血脉相连的骨肉深情,以及家国天下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正如陈大白所言,“这块位于珠江三角洲一个小角落、面积只有五平方多公里、人口仅十多万的半岛上,在前后四年多的时间,曾经出现过轰轰烈烈、激动人心、影响深远的抗日救国运动。澳门同胞和青年子弟就在这半岛上,亦在漫天烽火的华南前方,用丹心和热血谱写了一段不可磨灭的爱国运动史灿烂篇章”。